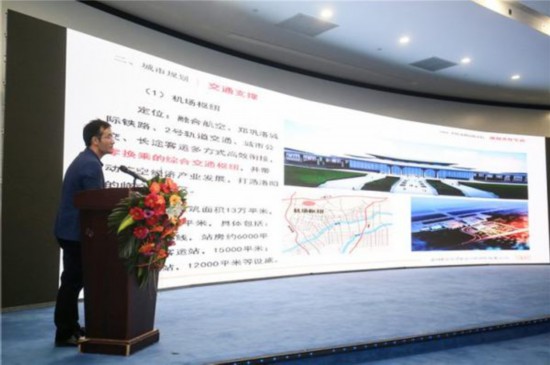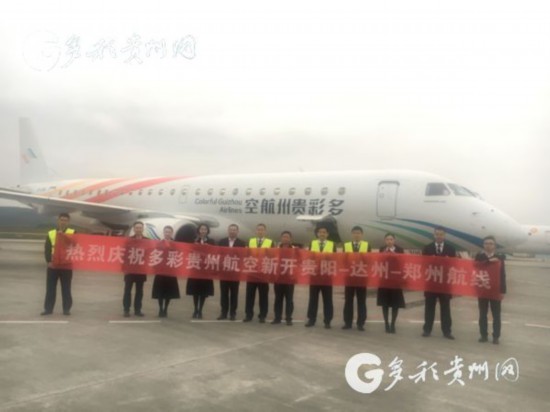英国作家麦克尤恩抵达北京 开启八日中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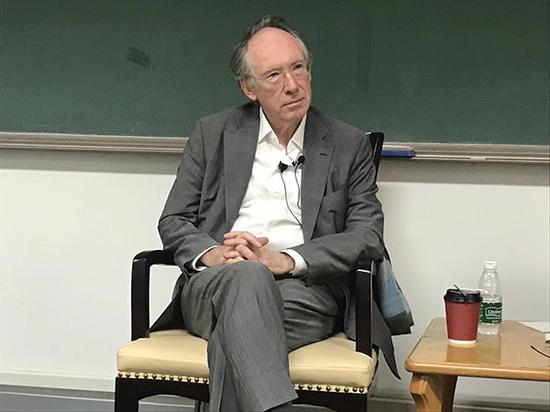
在课堂上的麦克尤恩
10月25日,英国作家麦克尤恩抵达北京,开始了自己为时八天的中国行。
在参加第三届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之前,麦克尤恩也与人大课堂与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学生聊了聊写作。
七十岁的麦克尤恩未显老态,谈吐举止温文尔雅,可能由于他小说过于光怪陆离,当怀着各种揣测去看向现实中的麦克尤恩时,倒觉得他过分友好和平静。但是在聊天时,言谈中还是透露出他幽默有趣的一面。
从《赎罪》《水泥花园》《在切瑟尔海滩上》《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近年来的《追日》《坚果壳》......创作力依然旺盛的伊恩·麦克尤恩,某种层面上几乎定义了读者们对英国当代文学的全新认识。
麦克尤恩谈在自己的工作状态是每天九点就坐在桌前,需要喝咖啡,然后非常努力的先不看报纸,“但是一般都会失败”。“我喜欢一边有一个记事小本,一边是电脑屏幕,我可以来回用。如果我手上有一个手机,我会很难集中精神工作。我夫人用一个软件叫自由飞人,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好几个小时不能上网,只能集中精神工作,我写小说写到好的时候写到畅快的时候很难停止,我是逼着自己如果写的好就一直写下去,因为我知道顺畅的一段是会完的,所以如果写的很顺我就逼着自己不能停。”麦克尤恩说。

麦克尤恩和他的中国责编们
你可以走出卡夫卡,但很难活着逃出纳博科夫
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他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谈过很多作家对他的有影响,如他所言:“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
在现场,他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卡夫卡。“在卡夫卡之前,英国人写小说都是寻常的恋爱、结婚、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人的阶级等等。我惊诧于当时英国文学界普遍的沉闷。但是直到我看到卡夫卡,他写一个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上不了班,而不是变成甲虫这件事。我喜欢这种幻想内容和现实情绪的结合,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的。”
“而我喜欢纳博科夫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在我的写作时期中属于很晚的阶段,我喜欢和模仿是正常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必须放下,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想法。纳博科夫有非常伟大的风格,他的句子非常紧凑,如果是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且学习效仿,你很难活着逃出来,当然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囚犯。”
麦克尤恩也在游刃有余地从各个小说家写作中汲取营养,有时甚至可以戏谑地应用,“比如《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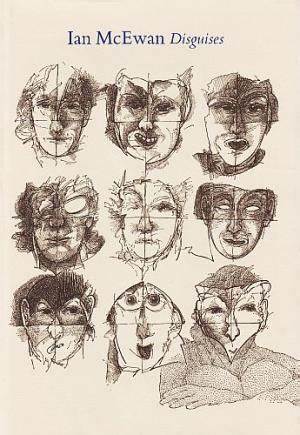
《伪装》
当被问起用多久的时间可以抛弃掉别人的影响,确立自己的风格时,麦克尤恩说:“七年。其实是五到十年,但是我很喜欢七,所以是七年。”
麦克尤恩谈到写作《坚果壳》是因为当时为了准备一个演讲,他重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的情节就进入了故事中胎儿的叙述过程,不知不觉地,《坚果壳》就成了哈姆雷特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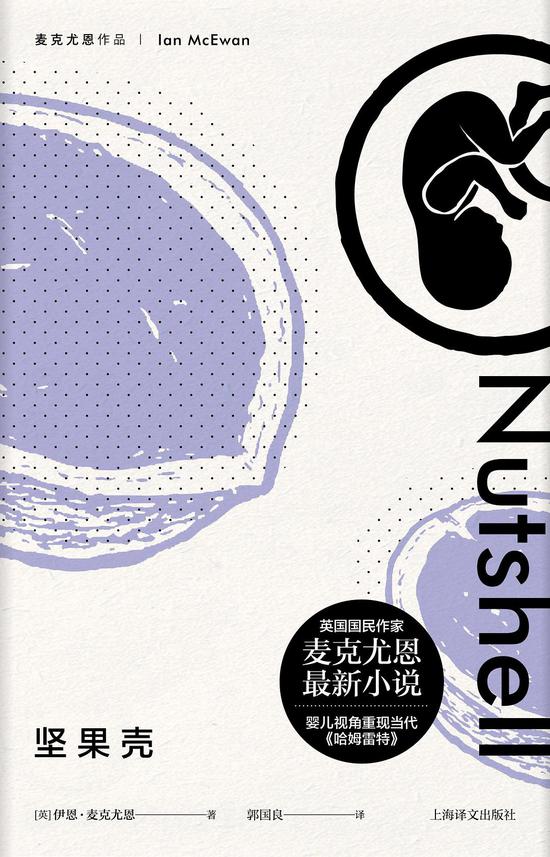
《坚果壳》
麦克尤恩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对早期人类的现代性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意义。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我们来说就像空气、阳光,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他的语言,可以分享他的语言,所以我用我的小说去重塑了一次我跟莎士比亚的关系。”麦克尤恩说,在自己的小说生涯中曾有好几次不再相信小说,觉得小说整个事情没有意义,但正是这些他钟爱的作品让他一次次相信小说的美好。
控制句子,给人物自由
麦克尤恩也谈到,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结构自己的小说。
“感觉现在新出现了一个需要解释你自己写的东西这样一个行业:你需要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去解释你的小说,但是其实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它不断带来惊喜,一个东西可以引申另一个东西的产生。小说的两个主要的元素像绳子拧在一起一样:情节会派生角色,角色会影响情节,这个技巧是非常复杂的。写小说最开心的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一个本来很边缘的角色发展得非常灿烂,或者一个角色的行为把你的情节拉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你写到最后你会完全忘记了发生的过程,所以解释真的很困难。”麦克尤恩说自己的写作就是控制自己的句子,但是给人物以自由。“我对我写下的句子有我非常坚持的控制,我写完句子的时候会不断回头看。”
但他表示,自己也很乐意听到评论家们的声音,他们有时候把作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尽管有的评论家是为了写而写。“我昨天知道,有中国评论家说,刚看到我的小说时,觉得我很邪恶,并说不想见到我。“麦克尤恩接着说:“我很期待见到他。”
关于所谓的“邪恶”,麦克尤恩也有自己的回应,他谈到自己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很多都是边缘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让他对自己的阶层产生焦虑,“在读当时的文坛大人物安格斯·威尔逊、金斯利·艾米斯和艾丽斯·墨多克的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计切入。我不了解他们描述的中产阶级世界,对西利托和斯托利笔下的工人阶级世界也完全陌生。我要找到一个与历史和社会都剥离的虚构世界。所以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我的气息,我的孤独,我对社会肌理构造的无知,连同我对融入社会肌理,发生社会联系的渴望。所以他们就这副怪样子出来了。”麦克尤恩在一次访谈中说。
麦克尤恩很强调写作时的“试错”:“有时我本来想沿着一个方向写,但是最后机缘巧合地偏离了,这种机缘巧合地错误也给我一些启示。”麦克尤恩也谈到,在小说《阿姆斯特丹》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或多或少的,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麦克尤恩说,即便他很努力地把写的小说和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个很大距离,回头看时,自己的生活还是以隐喻的方式藏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小说是很尴尬的事情,要打破这种尴尬是很难的。正如有人说过,没有人能写五百字的小说,而在其中没有暴露自己的性格。”麦克尤恩说。
但是不同于很多作家的一生跌宕,麦克尤恩过着迥异于他小说的一种平稳安定的感情生活:“过去22年,我有着非常愉快的婚姻,这个是要靠运气的,可能对有一些人,婚姻的体制是不好的,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七十岁的他,也有现阶段的思考,麦克尤恩说:“如果对世界失去好奇心就是灵魂的一种死亡,对于一个将近70岁的作家来说,我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如果有一天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减退,那我就应该退休了。”
现在麦克尤恩仍然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我最近就在思考,机器有没有它自己的意识,我也在思考政治,英国最近做出脱欧的选择,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报纸的瘾君子,好像是吸毒一样,我是不能一天不看报纸的。我对科学的兴趣也一直保留,不管生命科学还是物理学方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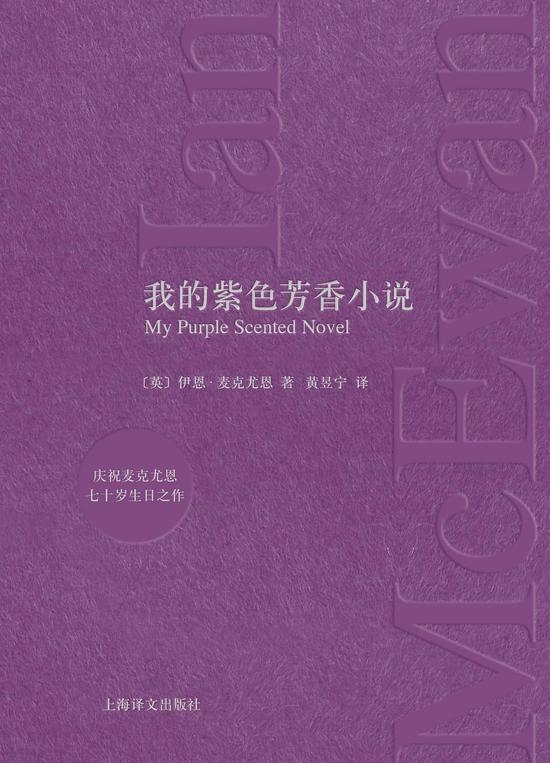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
翻译家黄昱宁谈到麦克尤恩的《我的紫色芳香小说》时说:“七十岁的麦克尤恩,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进入他最舒适的区域。主人公的年龄、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与他相仿。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这个故事当然关乎道德,窃名逐利者的逍遥法外,让人无法不被文学生态圈的荒诞所震撼——但它更关乎时间。在小说里,作者、读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黑色的,是讽刺的,但也是怀旧的,伤感的。”
她引用了麦克尤恩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深夜,我和他围炉而坐(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着酒,把这桩古怪的陈年轶事——这场灾难——翻出来,于是,他又跟我讲起了他那套经过多年打磨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他说,总是交织在一起。万事万物,我们都讨论过一千遍。我们读一样的书,经历过、分享过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象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熔铸在一起,以至于,最终,或多或少地,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10月26日,“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伊恩·麦克尤恩现场发表了以“数字革命”为主题的演讲,他说:当“人造人”写出了第一部有意义的原创小说时——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

伊恩·麦克尤恩 以下为麦克尤恩演讲全文:
我想要开启一段短暂的路程,踏入不可知的未来。我的出发点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已经发生的一项深刻的改变,而它影响的是这颗星球上的绝大多数成人,还有孩子。当然,我所说的就是数字革命。今天我们尚处在这场革命的初级阶段。也许历史刚刚完成了第一章。接下来的章节会更加深刻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我们自身的人性,进而影响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所有的艺术形式。此时此刻,这些新章节正在书写之中。
我这一代人,出生于20世纪中叶,成长于模拟信号的世界中。我们寄信,我们在公共电话亭里通话(信号很差);要想了解世界信息,我们会伸手求助书架上的百科全书。我们得到的新闻永远迟了一天。接着,我们不得不笨拙地过渡到一个数字宇宙中,为了应付各种数字任务,我们时常得求助于自己的子女,然后是我们的孙辈。
对于80后以及更年轻的人而言,他们成人之时,英特网业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那些被他们随身揣在口袋里的强大电脑不仅仅是有用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了自我的延展。因特网几乎已成为一个包围、影响意识本身的巨大精神体。我们学会了像在自己的脑海中漫游一样漫游于网络空间之中。我们与朋友,与广阔的信息世界的连接速度同步于我们思维的速度。英特网成为了我们的存储空间,成为了雄心、知识、关系、梦想与渴望的中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从学生到总统,没有了互联网,工作——甚至是生活——都是不可想象的。它以它最美好的面孔和最丑恶的形态囊括了人性。它囊括了我们。一旦由于某种技术原因丢失了网络连接,我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独,感到失落。这种奇怪的感觉完完全全是现代性的。它代表了人类意识的一次转变。
但这仅仅是开始。过去十年间,我们目睹了计算机科学的一场革命。人工智能时代已经降临。25年前,一台计算机打败了一位国际象棋大师。那台计算机的程序中塞满了数千场象棋赛。每走一步棋,它都会演算出每一种可能性。但就在去年,另一台计算机仅仅被输入了比赛规则和要求取胜的指令。除此之外,别无其它。比赛开始了,它下出了一步又一步非同寻常、步步见血的妙招,而这些绝不是人类能够想出的招数——譬如说,开局弃后。一台机器再定义了人类的游戏。机器学习已经进入了第一个兴旺期。利用算法,基于我们之前的购买选择,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给我们提供书籍电影网上导购建议了。它还能够规划商业航班线路。它还将在自动驾驶设计中大放异彩。
这一切会通向何方呢?许多个世纪来,在许多种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梦。那个梦就是创造出一个人造版的我们。就像基督教的上帝用黏土造出第一个人那样,如今我们自己或许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上帝,造出我们自己的第一个人造人。一千年前,在欧洲大大小小的教堂里,有的雕像会在某些特殊的日子里,为人类的错误和罪孽而落泪。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神迹——一尊上了油彩的石像竟然活了过来!如今我们知道了——雕像里面藏着一个水槽,里面有一条金鱼。金鱼一游动,水就会顺着一根隐蔽的管道流到人像的眼睛里。

19世纪初叶,一本小说诞生了,它成为了后来一切的文本基石。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与该书同名的科学家如何造出了一个人,用电赋予了他生命。弗兰肯斯坦的造物最后成了一个杀人犯。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告诫我们科学创造最终可能让我们玩火自焚。
我们生来就有一种将生命投射到无生命体上的本能。一幅最粗陋的人脸画也能把婴儿逗笑。谁没有在汽车打不着火的时候恨不得踹它一脚呢?一位哲学家曾经对我说,我们能够与一台冰箱建立起情感联结。但如今我们看到,未来我们也许真的能造出可信的、智慧的类人体,许多年来,我们的小说与电影一直对此浮想联翩。我们的新表亲或许一开始会成为孩子们的玩伴——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了这类产品的初级版。机器人可以帮助照料老年人,在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日本,这件事正在成为现实。科技已经造出了栩栩如生的皮肤、眼睛、头发;今天的机器人已经可以跳舞,甚至可以接球了——这件事并不像我们看来的那么简单。要设计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使用语言的软件则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而最最艰巨的任务则是创造出所谓的通用智能。但这一天会到来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何时到来。
也许这一天到来得不会像我们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快。人工智能让我们了解到,大脑究竟有多么神奇——一台只占一升空间的水冷三维生物计算机。它包含了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平均产生7000条输入与输出信号。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而这一切的耗能只有25瓦——相当于一个小灯泡的功率。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远远达不到这样的微型化程度,更不用说还要同时避免元件过热问题了。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到储存电能的高效途径。你在网上看到的那种笨重的机器人通常都插着一根电源线。不接电源的话,它们蹦跶不了多久就得充电。
还有,我们很容易忘记一点:象棋和生活不一样。象棋是一个封闭系统。比赛的历史与现状都确凿无疑。比赛的结局也确凿无疑。而生活却是一个开放系统——在各个层面上都不可预测。语言也是一个开放系统。要理解一个句子,我们必须调用关于外部世界的先验知识。要理解词义,语境是至关重要的。
但无论如何,那一天会到来的,人工智能会出现在笔记本、台式机与大型计算机中——它们还会帮助人类设计先进的人造人——因为我们无法抗拒那个计划的诱惑,那个古老的梦想,尽管依照我们自己的形象制造一台机器或许并没有太多的科学价值。但我们也可以说,孤零零的一台笔记本,一台没有躯体的计算机永远也没法同我们建立起一丝一毫的相似之处,它们既无法了解理解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们。

随着硬件与软件的进步,我们将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当一个人形物带着善解人意的表情 ,温暖的声音,有智慧、有见识的举止出现在你面前,而你知道这个造物就是在北京附近的一座工厂中生产出来的时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你的新朋友真的和你一样有意识吗?还是说,那只是他的设计带给人的错觉?他真的有自我,有悲喜,会怀恋过去,期待未来吗?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粗浅的应对方法。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图灵在1930年代 认真思考过机器智慧的问题,我们不妨采纳他提出的理念:如果你根本没法判定一台机器是否有意识,那你不妨就假定他有意识。毕竟,我们所有人类都必须假定彼此有意识,可我们从来得不到这一点的最终证明。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应对机器意识的难题——但我想把这一点留到最后。
归根结底,思维所依附的人脑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是由你的大脑和人造人的“大脑”所共享的。近100年来,理论物理学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物质比常识所以为的要奇怪的多。当我们最终发展到能够接受生物大脑相对于无机物大脑并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或特权时,我们立刻就会面对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授予人造人以公民权和公民义务吗?买卖或拥有这样一个造物是否是不道德的,就像过去买卖或拥有奴隶是不道德的一样?摧毁这样一个造物是否构成谋杀?他们会不会变得比我们更聪明,抢走我们的工作?在我们今日的工厂里,聪明但没有思维的机器已经开始替代工人了。下一个也许就轮到医生和律师了。接下来就是那个终极问题:人造人会征服我们,甚至是取代我们吗?
这些正是科幻小说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终于到了需要回答的时刻了。未来已然降临。我们可以赋予一台计算机怎样的道德准则呢?自主,自动驾驶车辆的生产商们已经开始面对这件事了。你的新车应该忠于谁呢?一个孩子突然蹿上马路,正好蹿入了你的行驶路线。如果你勐打方向盘,一头撞上一辆迎面驶来的大货车,你就可以挽救孩子的生命。这个选择必须在须臾之间做出。大脑运转迟缓的人类不太擅长快速厘清这类问题。你新买的自动驾驶汽车可以遵照编定的程序,将你的生命安全置于其他所有人的生命安全之上。或者,它也可以奉利他主义和社会公益之名,准备好了牺牲你的生命。这是一个我们在设计汽车自动驾驶软件时不得不面对的道德选择。
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我们的童年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这颗星球上生活着数十亿人类,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和你的内心一样鲜活、真实、不言自明的精神生活。也许,这就是道德观在一个人的童年诞生的时刻,那一刻你开始理解每一个旁人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是真实的,就如同你对于你自己而言是真实的一样。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就得如何待人 ;你还得试图理解一个不同于你的他人 究竟意味着什么。

日本科研团队探索人工智能写小说的项目。
这就把我的话题引到了另一项发明之上,一项古老的发明,不需要电池驱动,也无需高深的科技,但在道德上和审美上却高度复杂,当它登峰造极之时,美得无以伦比。我说的是各种形式的小说。要想进入别人的思想,要想衡量不同人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容纳它们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小说依然是我们最好的途径,最好的工具。小说家是在他人的思想之海上扬帆的水手。电影直观易懂,也很引人入胜,但它并没有像许多人预言过的那样让小说消亡。只有小说能呈现给我们流动在自我的隐秘内心中的思维与情感,那种通过他人的眼睛看世界的感觉。
如果我们真的准备好了——也许就在本世纪——创造出全新的有意识体,而他们的思想会渐渐踏上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道路,那么小说就将是我们借以理解他们的最佳途径。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种艺术形式,我确信它可以进入这颗星球上任何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头脑中。因此,它也可以进入一个类人机器人的头脑中。小说可以尝试着预演我们未来的主观意识,包括那些我们所发明的头脑的主观意识。在我们争论究竟应该给我们的造物注入何种道德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对并阐明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我们想要什么。而当一个人造人写出了第一部有意义的原创小说时——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们将有机会通过我们所创造的这些“他者”的眼睛看见我们自己。这将确凿无疑地证明一件事:一种全新的,有意识的造物已经降生在我们身边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将就此展开,无论它带来的会是美好还是恐怖。
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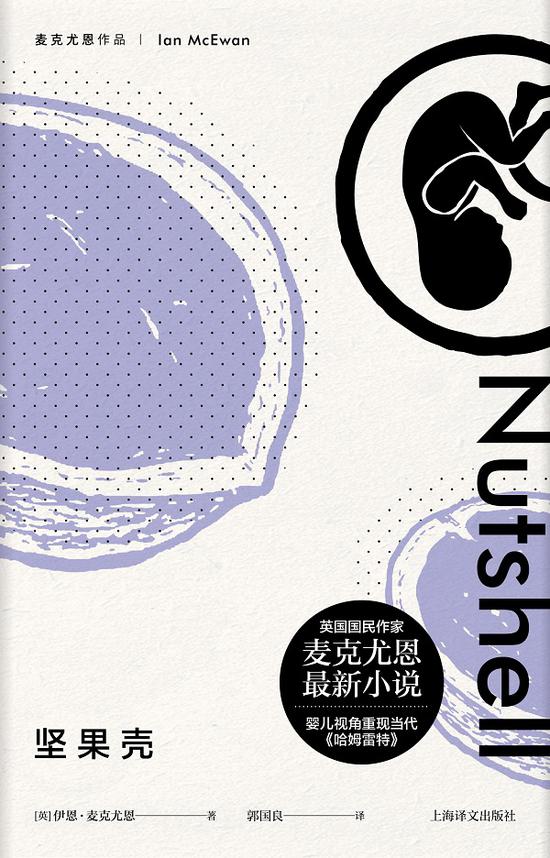
《坚果壳》
10月27日下午,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与中国作家格非以“大众媒体时代的虚构叙事”为主题展开对谈。对谈中,麦克尤恩对当下时代背景中小说的意义做出了精辟的解读,也对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做了小小的“剧透”。

小说家是站在真假信息风暴中的人
在过去,人们需要阅读小说来了解远方的故事。然而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跨越了时间和地域上的种种隔阂;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一一出现,让人们即使相隔千里,也能与事发地的人们同时听到最新的故事,小说的存在似乎变得不再重要。然而麦克尤恩认为,尽管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被人们看作最好的信息传播方式,但如今这种对互联网的乐观情绪正在慢慢消退,而充斥全网的虚假消息成为了新的时代困惑。过去那些文化素质很一般、只会在火车站前兜售理论手册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可以把他们那些虚假或很荒谬的言论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战争手段——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散播不实的信息,干预到另外一个国家政治的进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小说家该何去何从?麦克尤恩认为,小说家是站在真假信息风暴中的人。他说:“在过去,小说的主要作用是探究人心,揭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到今天依然是小说的主要功能。这一生中,’小说的时代结束了’、’小说即将灭亡’的预言我已经听到了很多次,但我认为小说还是会继续存活下去。因为小说能够在巨大的真假信息风暴中找到一个静止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上继续探究人心,继续研究所有的真相和谎言。”
此外,格非提到,前一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主题演讲中,麦克尤恩对小说的社会功能做出了深刻的思考。麦克尤恩认为,小说建立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极其丰富的场域;小说作者的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为不同的声音、思维和情感提供了广泛的交流空间。即便人们并不赞同彼此的观念,但依然能够被小说的叙事打动。格非认为,这正是小说的力量所在。
新作探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主题演讲中,麦克尤恩对当下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广受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做出了精彩的解读,而他刚刚写完的一部小说中也引入了科幻的元素。不过麦克尤恩表示,这并不算是一部科幻小说,因为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已经逝去的1982年,而不是未来,他稍微改变了当时的科学进程和政治局势,小说中1982年的科技比现实更先进一些。
麦克尤恩透露,小说的主人公买回了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后来爱上了他的女朋友。“这种三角恋肯定不是新颖的科幻题材,它是人们已经写得很滥的情节了。”麦克尤恩笑道。他进一步解释说,小说探讨的是机器人是否会有自我意识、人工智能究竟需不需要有道德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日常生活的迅速渗透,这些都是当下人们经常讨论的、在现实中已经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所以我这本小说,与其说写的是未来,不如说写的是现在。我认为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写的就是当下。”麦克尤恩说。

在庆祝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30周年的研讨会上,麦克尤恩曾提到一个词,叫“第三种文化”。当天在对谈现场,麦克尤恩对“第三种文化”做出了更详细的阐释。他解释说,“第三种文化”的概念出自约翰·布罗克曼几年前创立的网站H.com。“第三种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在各个领域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都开始向大众进行科普,并以人人都理解的浅显语言解释他们领域的新的发现。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进入社会人文领域,促使科学与人文学科出现交织,影响到政策的制订、社会问题的发展,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前文所述的人工智能正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麦克尤恩指出,科学家借用传统的人文学科手段进行科普,促使人文学科与科学找到了共同的平台,能够一起讨论社会以及政治问题,这种变化正是科学和科技的变化和进步带来的。尽管很多人文学科的专家学者并不了解“第三种文化”的概念,但有关“第三种文化”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并且越发蓬勃。